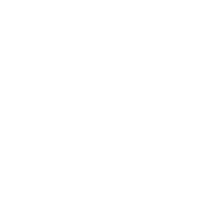《写作》新刊︱张利伟:韦敏小说中的纪实表达与自我书写
2024-06-25 本站作者 【 字体:大 中 小 】
武汉籍旅澳作家韦敏自《蓝花楹》后,完成了写作的转型。在经历亲人离世的创伤与岁月的磨洗后,其作品多以“自我”为切入口,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呈现出自传性、回忆性写作的特征。同时,其采用“编年体”叙事的方法,书写真实的历史细节;并以超越小说时间的作者声音合理介入,来增强小说文本的真实性。
韦敏,资深媒体人,1972 年出生于湖北武汉。1989 年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学习。2000 年后旅居澳大利亚。曾申请获得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文学博士候选人资格,研究亚洲女性的文学创作。2005年,其小说《没人知道我爱你》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此书被评价为“中国版的《欲望都市》”;同年,长篇爱情小说《巴黎爱情》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此书又名《米卡》,曾发表于《收获》。与其子韦斯理(Wesley)合著长篇史诗小说《蓝花楹》(武汉出版社2019年版),此书由韦斯理构思于2014年,韦敏定稿于2016年。2020年,韦敏本想继续创作《蓝花楹》第二部,却因疫情滞留在澳大利亚,同时,她开始创作《我无法证明岁月有脚》,该小说发表于《收获》(2022 年春季卷)。2023 年,韦敏长篇小说《丛台别》(缩减版)发表于《当代》杂志(2023年4月),其单行本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韦敏的创作以历史小说《蓝花楹》为界,前期主要是爱情小说的写作,且这些小说在发表前多发布于网站上。从《蓝花楹》开始,韦敏的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类是历史小说的创作,另一类为带有自传体性质的小说创作。韦敏一方面继续完成其子韦斯理的愿望,讲述澳大利亚的百年历史;另一方面,经历了彻骨的生死离别,与故乡的隔离,旅居澳洲的她又开始书写武汉的历史,以其独特的“武汉伢儿”的视角,书写着汉剧中的武汉风情剧。从书写女性情欲追求的女情小说《没人知道我爱你》,到更为深沉地探讨小人物“米卡”的国外生存境遇与爱情追求的《巴黎爱情》,再到历史小说《蓝花楹》与带有历史小说性质的汉剧小说《丛台别》,以及颇具自传性质的个人成长小说《我无法证明岁月有脚》,韦敏在不断拓宽自己的写作领域。2015—2016 年,其子韦斯理生病离世大约是其创作转型的一个动因。韦敏不止一次在创作谈中提到了其与韦斯理的对话:
韦斯理问,妈妈,你说,这个世界上买得起宝马奔驰的人,和能够出版一本有分量的历史小说的人比起来,哪个数量会多一些。
而当2020年,韦敏滞留在澳大利亚时,她的父亲因病去世。韦敏开始写作《我无法证明岁月有脚》,为了纪念,为了在文字中,让那些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重新活一次。所以,她并不忌讳纪实性的书写,反而以回忆者的姿态面对这个沧桑巨变的世界。“纪实”对于韦敏来说,是同自我书写相联系的。韦敏在继续自己作家梦,也在实现其子韦斯理的作家梦。正如她在《蓝花楹》中提到的:“所有过往,皆为序章。”文字,让所有离去的、故去的,重新鲜活。
本文主要探讨韦敏转型后的写作,其创作其实出于一种不得不写的冲动,这也是我们在2019年看到韦敏作品不断面世的原因。作为一名“说话”的女性,作为一位伟大的母亲,作为武汉籍的旅澳作家的韦敏,育有三个孩子之后,有了更多的生命体验,而这种体验,正如其在《丛台别》中讲到的“时间是贪婪的,它带走了美好的故事,还吞噬了所有的细节”,而她能做的就是“快醒来,快点儿,记下这些话,不然就什么都没有了”。当然,小说很容易带上作者个人生命体验与人生经历的色彩,民国时,郁达夫、萧红、沈从文等多有自叙性质的小说的创作。如郁达夫以自己日本留学的经历为基础,表现其身体苦闷与心理苦闷;沈从文的早期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合成了一部沈从文的‘自叙传’”;萧红“以个人叙事的方式介入时代话语,呈现充满日常经验的审美表达”。而我们通过韦敏的小说,结合其独特的人生经历,也大致能够勾勒出充满小说意味的自叙传。充满自传和回忆性质的自我书写,以及结合真实与虚构的叙事,构成韦敏小说的特色。需要着重思考与讨论的是其回忆性的自传写作,带有纪实性的时间描写,如何框定在以虚构为主的小说之中;进而言之,其真实、虚构的界限又在何处;其创作主要采用了何种叙事策略,这种策略又如何加深了韦敏小说的回忆性质。
韦敏是个从大学开始就有“作家梦”的人,移民澳洲以后,曾申请获得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文学博士候选人资格,研究亚洲女性的文学创作。但是,相比于“做学问、尤其是用非母语的文字工具来从事文学评论”,她选择了创作。而她在生活中积累的小说素材,从“自我”到世界,也呈现在了其小说之中。
首先,韦敏小说中主人公的设定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其小说中的主人公拥有着相似的经历。《没人知道我爱你》主人公殷拂与《我无法证明岁月有脚》主人公梅亦可、《丛台别》主人公程米粒均为1972 年出生,1989 年考上武汉大学,毕业后进入电视台工作,或担任时尚杂志编辑,或在出版社工作。《丛台别》着重写了韦敏初高中时期的记忆,《我无法证明岁月有脚》写的是大学时期;小说主人公后来的工作经历都融合了作者作为传媒工作者的经历。至于《巴黎爱情》的写作,韦敏谈到,“我曾在巴黎生活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因此,这个故事的大背景和人物的生活细节,有着扎扎实实的现实基础”。《没人知道我爱你》则结合了她移民澳洲的过程,以及澳洲生活的经历。
而这些与韦敏个人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只不过每一部小说都是其不同生命历程的“记录”。作者试图用小说书写自己的不同侧面,当女性转向心灵与生命的探索,其笔触往往不自觉地以“自我”为切入口。齐奥朗《在绝望之巅》之中写道:
人并不学习心理学这门技艺,而是以生活和体验感悟它,因为没有什么科学能给你解开灵魂奥秘的钥匙。如果不把自己变成研究对象,不对自身情况的复杂性表现出惯常的兴趣,就不能成为一名像样的心理学者。要进入他人的奥秘,你必须首先进入自己的奥秘。要做一名心理学者,你必须足够不幸,才能理解幸福,要能随时做一个野蛮人,才能如此文雅,你还要陷入强烈的绝望,以至弄不清自己是生活在荒漠中,还是火海中。你那变化无常、向心和离心程度相当的狂喜,必须是审美的、的、宗教的、反常的。
以自我为研究对象,是心理学的一个入口。以文字来书写自我,也是创作的一个切入口。小说中的主人公与现实生活中的韦敏,看似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幸福”,然而与亲人别离的苦痛以及关于已逝岁月的记忆,构成了她书写的主题。她通过文字与韦斯理对话,与父亲对话,这可能也是近几年其创作厚积薄发的一个原因。其三十岁左右创作的两部小说,以女性的爱情为书写对象,详细剖白了女性在爱情中的追求与欲望(《没人知道我爱你》),以及男性视野观照下身处法国底层的偷渡女子“米卡”的不幸与悲哀(《巴黎爱情》)。韦敏从自我出发,经历生命沉浮,沉入岁月的荒凉,而后在写作与文字中重新回到生活,中欧体育最新地址回到自我的历史,以小窥大地呈现“70”后的成长史。也因此,我们也能在其众多小说中看到作者的影子。作者似乎擅长书写回忆性质的文本,而且在叙事逻辑上也大多以时间脉络推进,正如克里斯蒂娃所言:“因回忆导致的癔病(男人的或女人的)更多地从先前的时间形式(循环的或永恒的)中识别自身。”写作是另一种形式的“癔病”,在作者与自我的对话之中,在强烈的自我剖析、追索中,实现了生命的摆渡。所以,其小说通过人物、情节等的设定表现自我生命历程中恒久的话题,如成长与别离,与亲人的别离、与母亲的远离,等等。
深入其文本内部,我们也发现,不只是主人公人物设定的相似,如《我无法证明岁月有脚》《丛台别》中,均有强势的母亲(中学教师)与妥协的父亲(大学教师)。在对待女儿的男朋友时,小说中的母亲,不论是对来自新疆农村、没有什么见识、长相也一般的董梁,还是对小有名气的唱歌艺人冷堃,都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而不管是程米粒还是梅亦可,对母亲都呈现出了一种复杂的心态。
其次,小说中的故事情节也在相互引用、借鉴,构成了某种“互文性”。“互文性”最初由克里斯蒂娃提出,随后受到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符号学、解构主义等的关注。在蒂费纳·萨莫瓦约看来,互文性和复调一样,都是一种文本内部的对话,“文学作品总是在和它自己的历史进行对话”。将文本与作者剥离开来,就文本内部而言,我们能看到韦敏的文本自身互成体系且相互关联,而这在带有回忆与自传性质的小说《我无法相信岁月有脚》以及《丛台别》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前所述,《丛台别》着重写了韦敏初高中时期的记忆,《我无法证明岁月有脚》写的是大学时期。自传色彩是其小说内部文本持续对话的一个根源。热奈特也在《隐迹稿本》中将互文性定义为“两个或若干个文本之间的互现关系,从本相上最经常地表现为一文本在另一文本中的实际出现”,热奈特进一步将互文性分为五种,其详细解说了第四种类型“承文本性”,即联结文本与另一文本(蓝本或元文本)的“非评论性攀附关系,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嫁接而成”,承文本通过嫁接、模仿或改造,往往比元文本更富有文学性。由此,我们探讨韦敏不同小说之间的文本关系时,发现其具有元文本与承文本的性质。但在这种对比中,我们无法确定哪一个文本是蓝本,哪一个又是更富有创造性的小说文本,这两本小说的创作时间也大致相同,只能说作者在书写不同时段的回忆,且这些回忆以自我或身边人为原型,但有虚构的成分。这两部小说中的事件与情节构成了显见的互文。如《丛台别》中提到了程米粒大学时期的男朋友为擅长写诗的88 级学长“邰风”,只寥寥数语,且是描写邰玉故事的一个“背景板”。而《我无法证明岁月有脚》用大量的篇幅叙写梅亦可与擅长写作现代诗的88 级学长董梁的爱情故事,其与梅亦可从相见、相爱到相别,占用了大量的篇幅。《丛台别》中,并没有直接的叙事,而是以程米粒的心理活动,表达了其对这段感情的留恋,“她读着他为她写的情诗,幻想着毕业后能马上成为她的新娘”。这种心理活动,在《我无法证明岁月有脚》中也有,梅亦可在返校的汽车上,“充满了对未来的无限联想:她应该会一毕业就跟她结婚吧”。
因而,作者并不忌讳人物设定的重复,相反,其一直在设定相同的人物,在书写类似的事情。弗洛伊德提到过“强迫性重复”,指在童年若是遇到无法弥补的创伤,在成年之后会继续重复这样的心理模式。当然,成年人遇到巨大的挫折与打击之后,也很有可能重复当时的情景。虽然人追随快乐原则,但此时重复原则占据了上风。讲述、书写是一种手段,不断疗愈童年、成年后经历的无法解除的创伤。韦敏将自我作为写作与研究的对象,在其写作中重复提到对母亲的顺从与反抗,丧失亲子的苦痛等,可能这些对于她而言,不只是一种小说素材,她以此建构自己的小说宇宙、重现过去的人生,再次释放与触及某些情绪与未完成的心愿。
复次,韦敏创作谈中体现的真实自我也进入小说写作中。韦敏《我无法证明岁月有脚》创作谈《在大地上,我们只过一生》谈到,有位高年级师兄曾推荐她看三本书,它们分别是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杜拉斯的《情人》和记载萨特与波伏娃人生历程的《心心相印》。在小说《我无法证明岁月有脚》中,董梁拿给梅亦可的就是这三本书;而梅亦可推荐给邹皖的也是《心心相印》。韦敏早期的作品《没人知道我爱你》也常常引用《霍乱时期的爱情》或者《情人》来发表自己的观点。这些现实中韦敏钟爱的书籍,在小说中也承担了隐形叙述的角色,它告诉我们,作者与主人公存在某种相似,让读者更加相信这是带有作者特色的、富有纪实性的故事。韦敏《在大地上,我们只过一生》中谈到父亲曾用大仲马夸小仲马的一句话表达过他对韦敏的期待——“你是我最好的作品”,这句话也被运用到《丛台别》中程教授与程米粒的谈话中。所以,在韦敏这里,我们常常会模糊真实世界与小说的界限,也正像她在《丛台别》中说到的“人生如戏”,她使自我与身边人入戏,而四散的记忆在其小说中终以入海。
本文所言的“编年体”叙事,并非史书中的以年纪事,而是作者在创作中有意按照时间顺序来推进小说进程。而且“编年体”叙事的命名,也借鉴了韦敏《我无法相信岁月有脚》中的说法:“我们按照编年体叙事的状态,现在需要讲的是她跟董梁的纠缠。”这种叙事策略与其回忆录式的自传书写是分不开的,也正是因为直线型的时间赋予了故事流动性,其小说创作精准地记录下每一个重大事件发生、发展的时间。如《丛台别》中,1978年,程米粒6岁的时候,邰玉被父亲邰汉生带着由汉阳前往汉口,参加汉口戏曲学校汉剧科的考试;1987 年的春晚,费翔表演了《冬天里的一把火》,钟爱费翔的程米粒三个月没吃早餐,省下五块四买下了《四海为家》的磁带,这件事也“点爆了”彭一方(程米粒的母亲),程米粒被惩罚后前往汉剧院找邰玉诉苦,得知邰玉即将赴日本表演汉剧《曾根崎殉情》。故事中的每一个事件,都是有明确的时间线的,多是按照程米粒的视角,让她身边的人物各自登上“九龙口”。
另外,历史小说《蓝花楹》也采用了这种叙事策略。创作《蓝花楹》前,14 岁的韦斯理“根据梅恩家族的族谱年鉴、经商史和关联人物绘制了一个大事年表,考察对照英国、爱尔兰和澳大利亚殖民时期历史同步记载的著名事件和人物,把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相关的人物和地点进行了横向交叉融合和特别标记”。韦敏在创作时,严格按照时间线来推动故事的发展。故事情节的设定,基于韦敏和韦斯理合乎情理的推测。在充满悬疑与解谜氛围的书写中,韦敏将体现真实事件的史料、照片等置于小说之中,也为小说创作增加了更多的真实性。“几乎所有的出场人物都是存世过的有名有姓的真实人物”,韦斯理与韦敏还亲自到小说可能涉及的历史遗迹,包括建筑、街道、雕塑、当事人墓地等进行实地考察。小说中出现的大量文献资料、图片资料都增添了故事的“真实性”。
不只是《蓝花楹》为真实的人物作传,发表在《当代》杂志上的《丛台别》,其主人公之一邰玉,也是以汉剧名角邱玲为原型塑造的。小说中邰玉比程米粒大3 岁。1978 年,邰玉参加汉口戏曲学校汉剧科考试。在程米粒上大学后(1989 年后),邰玉获得过“青年突击手”“三八红旗手”荣誉,二十出头就获得了中国戏曲类的最高奖“梅花奖”,并且参演汉剧《曾根崎殉情》,赴日本演出,在1993年前往中国戏曲学院学习。邰玉还曾赴日本短期交流。
方月仿《中国汉剧日本行散记》介绍《曾根崎殉情》的主演为邱玲和熊国强,另外,青年演员邓敏、刘丽也表演了节目。邱玲,出生于1969 年,湖北黄陂人,1979 年考入武汉市戏曲学校汉剧科,1986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武汉汉剧院,拜汉剧大师陈伯华为师。1987年获湖北省戏曲剧团青年演员比赛金奖。1992 年,获得第九届中国戏剧梅花奖。1993 年考入中国戏曲学院导演系本科班,1996年进入中国戏曲学院第一届青研班。1999年经中国戏曲学院批准,邱玲受日本同志社大学文学部邀请赴日本参加了三个月的学术交流活动。
根据以上活动,可知,作者是以邱玲为邰玉的人物原型。从名字上,也能看出端倪,“邱”中“丘”易为“台”,“玲”取“玉”,而成“邰玉”。作者在《丛台别》中对邰玉的容貌描写,也与现实中的邱玲对得上。邰玉在1988 年国庆节前,将要赴日本表演《曾根崎殉情》时,在品芳照相馆拍了生活照和定妆照。作者是这样描述邰玉的外貌的:
从那以后,只要逛六渡桥的人,经过中山大道时,都会看到邰玉侧脸凝思、嘴角微笑的那张逆光照。摄影师给她配了顶白色贝雷帽,小小的帽子倾斜着倚在她茂盛的黑发上,贝雷帽的下方,拖拽着褶皱着的白色的面纱。邰玉用她那能展现飞燕和孤雁神采的手,轻轻拈起面纱的一角,让面纱半遮半掩地挡住她的整个面部。面纱的网格兜住了从邰玉背后投射过来的柔光,像雾一般地把她面部的轮廓由外及里地渲染开去,最后的聚焦就在她那双闪烁的大眼睛里。在这张照片里,她的眼睛在说话,嘴角在倾听,手腕在舞蹈,头发在歌唱。
其服饰、姿势与神情,与韦敏笔下的邰玉高度一致。作者的描写,应就是以此照片为底本的。另外,《丛台别》中来中国的“戏痴”日本教授原田夕鹤,原型就是向井芳树。小说中的原田夕鹤为了方便指导汉剧院的活动,直接在武汉大学谋了教职。向井芳树在陈伯华表演艺术研讨会上的发言《陈伯华的歌声令人难忘》中提到:“我于1987 年到武汉大学任教……那次为了看庆祝伯华先生从艺六十周年而举办的演出,对邱玲、邓敏、王立新、熊国强等青年演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说中也提到了原田教授对邰玉的赏识。所以,我们能看到韦敏小说的书写,其实是以现实发生的历史事件为依据的,在真实的历史与生活框架下,韦敏通过细致的心理活动描写、生命体验注入,使其作品具有可读性。这也是小说与新闻报道的区别所在。
与“编年体”叙事相对应的是,韦敏小说中的叙事内容也充满了历史的真实细节。《丛台别》中讲到,1934 年,“梅兰芳在‘汉口大舞台’(今天的武汉人民剧院,已成为汉剧院专用剧场)演出了整整一个月”,“1951 年,中南军管会接管了六渡桥的‘新市场’,改名‘民众乐园’(就在原总部旧址南洋大楼隔壁),京剧大师梅兰芳应邀再次来汉”。根据梅兰芳口述《舞台生活四十年》,其第二次来武汉是在1934 年,“章遏云正在汉口组班,约我来表演演出地点就是汉口大舞台(现在的人民剧场),住的地点也就是德明饭店……演完了还转到新市场(现在的民众乐园)唱了三天”。根据《亦报》刊载的《汉剧分会欢迎梅兰芳》以及《我在汉口演出的情况》,可知梅兰芳自1951年4月23日至6月1日,在汉口演出五十余场。韦敏的叙述与当时的报刊记载、艺术家口述等一般无二。
同时,韦敏小说的叙事线年代的特色。在《我无法证明岁月有脚》开篇,作者便写道:1989年9月12日那一天,武汉大学所有入校新生在学校的“九一二”大操场集合,接受主题训话;而这个操场之所以有这样的名字,源于1958 年的9 月12 日毛主席曾在此接见过武汉的大学生代表。诸如“革命就是请客吃饭”等富有时代特色的话语,与武汉方言相联系,共同展示那一时代的武汉腔调。
身在澳大利亚的韦敏,不断书写武汉,在她的笔下,武汉的美食,一道一道展现在读者面前;武汉方言,一句一句回应着过去的事情。也许,正是因为在远方,才能更好地书写、怀念、回忆那消散在岁月中的味道、匆匆长大来不及告别的人。罗瑟琳·科渥德在《妇女小说是女性主义的小说吗?》写道:“‘自白小说’(confessional novel)也是当代小说所具有的一个要素,即小说的建构和叙述中的有意义的事件均围绕着主人公描述其生活的声音展开。”在对历史与真实的书写中,韦敏使读者看见了记忆中的武汉,也看见了遥远的澳大利亚。
现实生活中的时间常常以日升日落、一年四季的序列方式来呈现,但小说中的时间与空间却富有更多的可能性。在时间的涟漪下,作者巧妙丢置的“鱼竿”使得记忆的湖水下暗潮涌动。这个“鱼竿”就是或显或隐的作者声音,作者声音通过叙述呈现出来并介入小说或让小说自我显现。针对小说作者介入、显现有不同的说法,如萨特认为作者“必须提供一种他根本不存在于作品之中的幻觉”,巴赫金认为“作者在时间和空间上全方位地置身于作品之外,对主人公的整个生活作出最终裁判”。若要使小说自我显现,作者所需只是客观陈述,小说中的人物,自己决定了自己的结局。但是,我们在韦敏小说中看到的是韦敏借鉴了“元小说”的叙事方法,使读者相信作者拥有全知全能(或半知半能)的视角,其讲述的故事也是真实的。读者在“接受虚构文本的过程,就是不断调整自身立场、不断将虚构文本中的内容视为纪实文本的过程”。
作者参与会为小说发展提供叙事走向,敏感的读者可以通过作者或显或隐的话语,猜到小说的结局,而读者也在不断接受、参与叙述中,不断地接近文本。情节,以一种有意无意的方式进入读者脑海。比较有趣的是颇有悬疑性质的历史小说《蓝花楹》。其叙述者虽然是玛丽,但是作者在某些地方又会跳出来,以上帝式的全知视角来审视问题。而《蓝花楹》的叙述者,不只是小说中的“我”——玛利,这里的玛利包括双重身份,一重是正在经历情节的世中人,一重是作为回忆者的玛利,后者正如引子中所谈,为死去的玛利,回忆者玛利常常使用“许多年后我终于明白”“几年后的某一天”之类的话语,表明自我身份且给读者以提示。如《蓝花楹》第一章中玛丽在离开爱尔兰,将帮佣3 年的酬劳18 个英镑提前拿给母亲时,小说写道“直到很多年以后,我也开始张罗着把爱尔兰老乡运送到澳大利亚的时候,才知道如果想在澳大利亚本地找个劳工,每周的薪水大概就要0.5 到1 英镑,一年下来,少说也是30 英镑了”。经历事件的玛利为剧中人物,而叙述者玛利为半知半能,更深层的讲述者即作者似乎是全知全能的,但是作者只是偶尔抽离出来,偶尔以史料、文本形式来证明事件的真实性与历史的真实性。半知半能的叙述者(剧中人玛利),以对“秘密”的追索为移动视角,慢慢揭开柏曲克·梅恩藏于心底的救赎。柏曲克身上的众多“秘密”——疾病、杀人犯、遗嘱等,其实,有心的读者能从作者的叙述与剧中人玛利的疑惑,猜测到故事的走向,这也是作者为读者窥见虚构的历史真相打开的一道门缝。
除了《蓝花楹》中叙述者偶尔提前“透露”故事的走向外,《我无法相信岁月有脚》《丛台别》等小说中也使用了这种策略。《我无法证明岁月有脚》中,梅亦可在军训时,因教官不由分说便惩罚全排女生而怒砸饭碗,这个时候,作者写道:“但是,数年之后,她真的砸掉了自己谋生的‘铁饭碗’时,她忽然就联想到这个军训的早晨,联想起那天怒气冲冲地砸掉稀饭碗,她想,生命中的一切,冥冥之中都有迹可循。”这些是作者对故事情节的提示,提示读者这些故事可能是真实发生的,因为它隐含于作者叙述,读者跟随作者的视角,先于剧中人物知道故事的情节与走向。而此亦加深了小说的自传性质与个人色彩。
这种旁观介入的叙事方法还呈现在小说整体的架构上。《蓝花楹》“引子”便表明此书是玛利的回忆录,“承载着世人无限的仰慕与妒意,也忍受着比鞭尸还残酷的唾弃”的玛利,现在安静地躺在墓地之中,她的孩子现在也躺在她的身边。这是玛利的叙述,更是作者视角想要呈现的玛利。我们从这里便知道了故事的结局。《丛台别》单行本也是以彭一方(程米粒的母亲)因投资而丢掉了几十万元的情节作为开始,详细展开过去近百年间的故事。《我无法证明岁月有脚》开篇写道:“故事要从1989 年说起,这是个巧合,……一切似乎源自光阴之变,而所有的时光指向,让他们最终变成了——连自己都不认识和不认同的一群人。”从小说最先的叙述中,读者可以感知到,作者了解所有的情节。整体叙事包含着“反向预言”,“是时间系列的结尾——事情最终演变成了什么——决定着是哪一件事开始了它:我们正是因为结尾才知道它是开端”。
作者介入故事,但是更多的时候,给予小说中人物以自由,给予其自由探索的空间。《我无法相信岁月有脚》相较于《丛台别》,叙述之自我显现更多。虽然二者均为第三人称叙事,但是《我无法相信岁月有脚》中的几个女主人公,梅亦可、宋微、易瑾三者似乎处在平行世界,作者是以全知视角来讲述,但是作者其实只站在了梅亦可的身后在旁观。作者与梅亦可一样,对宋微、易瑾真实的心理活动以及事情的具体细节充满诧异。小说的发展更多地在客观叙述中展开。而《丛台别》虽然也是以程米粒的视角展开,但是程米粒参与并旁观了汉剧名角邰玉以及媒体人江淼二人的生活,并且作者通过描写邰玉、江淼等的心理活动,透露了未来的走向,消除了读者对除了程米粒之外主人公的陌生感。可以说,作者介入的程度更大。
不管介入程度大小,作者声音与小说内部时间都形成了一个有趣的联结。作者声音时而以介入的方式超越小说的时间,时而以描述的方式展现小说时间。小说中的时间也以小说中人物的心理时间而非现实时间为尺度。当然,现实的时间只是被规范化的时间,人类对时间流逝之感悟,也与经历、情绪等相关联。当韦敏遇到需要重点书写且对主人公成长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时,其小说中的时间就会放缓,同时,很可能以一种介入的方式发出作者声音,提前告知读者这件事的结局。比如《我无法相信岁月有脚》中砸掉铁饭碗的事件,这个时间点被反复描述,而随后的故事也大致按照作者提前发出的声音而展开。所以,虽然采用了“编年体”叙事,但是其合理介入或展现的方式,使得真实与虚构并行不悖。作者合理的发声,既在时间之中,又在时间之上。
在韦敏看来,自己生活的真实与过往都是小说的合理素材。当我们讨论韦敏小说中的自传色彩与个人色彩时,其“编年体”叙事以及对历史细节的真实描写等,也使得小说更加真实可感。在完成回忆书写与历史纪实的书写后,韦敏又通过跨越小说时间线的作者声音介入,使读者将虚构文本逐渐视为纪实文本,不断接受其叙事逻辑。
其实,真实与虚构对韦敏来说可能并不重要。当被问及《我无法证明岁月有脚》是否有自传色彩时,韦敏不置可否,“太多人与事没法坐实,但又分明是切实的”。来颖燕评论道:“真实与虚构的边界因此注定只能是虚线,因而回忆的天地会有足够的包容力——可以杂取记忆力的种种遭遇,自己的或身边人的,亲历的或是听闻的,最终这遭遇由谁认领并不重要。”在创作《蓝花楹》时,韦敏提到“人物关系、人物冲突和人物性格,乃至主人公的个性缺陷与猝然去世的病因,完全都是顺应历史的脉络、人情逻辑和科学依据”推理出来的。张箭飞评价《蓝花楹》“文学自由的想象与对真实的专注高度咬合足证这是完全迥异于一般澳洲华人写作主题的叙事策略的一部小说”。我们可以看到,其以真实的事件为基础,搜集新闻报道、图片,进行实地考察等,并且对历史或记忆中的事件进行移植或合理推论,这也形成了韦敏小说的创作特点。
除了历史小说《蓝花楹》与早期的爱情小说《巴黎爱情》外,韦敏的小说也多呈现出生活化的结局,具有某种开放性。正如苏珊·格巴在《“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中所言:“许多妇女作家所写的书,之所以不可能有真正的结局是因为主人公的生活——同她们的作者一样——正在继续着,或是有着开放性的结尾。”这并非创造性的局限,而是因写作主题而产生的不同的叙事策略。韦敏的写作源自回忆,过往皆为写作之序章。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

猜你喜欢

《时尚芭莎下半月刊》征订【2017年杂志征订通知】
 933
933 
穿搭小白也能轻松变时尚达人
 561
561 
节日时尚达人跑酷(FashionFestival Runner)
 796
796 
新闻简讯电子书电子书报价评测天极网频道
 941
941 
“2021中国国际时装周”如期举行——中国线下走秀振奋全球时尚产业
 847
847 
迪丽热巴 BAZAAR 产品广告片全新封面解锁上线
 890
890 
时尚达人 EZpad 4s
 818
818 
2013年中国服装网或将全面改版
 836
836 
赵丽颖时尚芭莎八月刊内页图集!秀复古风尚漂亮的像是油画美人
 725
725 
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携手北京国际设计周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515
515